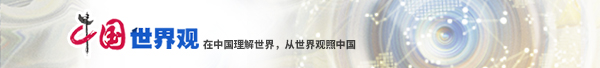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两个出现频率最高的核心关键词——“制度”和“治理”。从一定意义上讲,把握了这两个关键词——“制度”与“治理”关系逻辑,就是把握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上的中国的发展。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与治理关系,有必要系统总结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比照传统治国之道中的政道与治道关系,从中分离出有益于精准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制度与治理关系的有益因子,进而推进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具有丰富的制度性精华
中国是一个有着丰富的治国传统和治国经验的国家。自古以来,“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广大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政治抱负和人生追求。他们不仅躬身笃行,以治理好中国这个泱泱大国为己任,而且十分注重总结经验,留下了丰富的治国经典。东汉政论家荀悦将传统中国的治国经验概括为“兴农桑以养其生,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统其法”,其中涉及民生、道德、文教、军事、法制五个方面,称得上是传统中国治国之道最简明、最精辟的概括。
总体上讲,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是以“德治”为核心的治国之道,但也有制度性精华。比如《礼记·礼运》在谈到小康社会时,既强调了“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和“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立田里”“贤勇知”等德治的内容,同时也强调“正君臣”“设制度”等带有制度性的内容。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曾形成过各具特色的政治与行政制度,正是这些制度推动和规范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发展。
关于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战国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商鞅就有过经典的论述:“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抟也。制度时,则国俗可化,而民从制;治法明,则官无邪;国务壹,则民应用;事本抟,则民喜农而乐战。”他将制度、法治、国务作为治国的根本,并强调了三者之间的依存和推进关系。至于中国古代在调节中央与地方行政制度、中央与地方财政制度、政治与行政决策、执行和监督制度方面,也是多有建树,不乏制度建设范例。
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制度建设(特别是行政体制)方面曾经取得过丰硕的成果,留下了诸多制度性精华。比如,无论人们怎么评价,中国的科举制都是中外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人才选拔制度。它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代,衰于清末,延绵存续了1300年,产生了700多名状元、11万进士、数百万举人,秀才更是不计其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大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中国科举制度对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播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也是世界上最具特色和最严密的监察制度。从西周的监国到明朝的都察院,中国的监察制度越来越严密和规范。比如,明代除了正常的监察机关——都察院外,另按行政六部体制设立六科,直辖于皇帝,负责对六部官员的经常性监督。为了防止监察官员的舞弊行为,都察院与六科官员之间可以相互纠举,都察院内部都察御史和监察御史也可以相互纠举,这就使得监察官员本身也处于被监察的地位。
传统治国之道重“治道”而轻“政道”的偏颇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重视行政管理的传统。《左传》中即有“行其政事”“行其政令”的说法。孙中山先生认为“政”(即政治)是众人之事。“治”(即行政)是“治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是没有政治的,因为在专制制度下,有的是“国事”,而“国事”实际上只是“君主之事”,而是没有“众人之事”的。因此,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就是试图改变这种专制的政治体制,进而建立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
就政治与行政过程来说,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也是重“治道”而轻“政道”的。从孔子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到老子所推崇的“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直至孙中山先生概括的“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这里所说的“政”“政治”,很少涉及权力和体制问题,多是指为政之道,近于策略和方法,均属于“治道”的范畴,即“行政”的范畴。以治代政,以行政代替政治,乃是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特色。
在中国古代政治体制中,不仅政治与行政不分,而且行政与财政也是不分的,甚至行政与司法也是不分的。比如,宋代大清官包拯就既是秉公执法的判官,也是执掌行政大权的开封府尹,还是开封府财政的最大管家。至于中央朝廷的皇帝,更是集立法、执法、行政、财政甚至宗教大权于一身。这既是君主专制政治的重要特点,也是君主专制政治存续的内在要求。
当然,这种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现象与行政机关和行政权力的基本特点有关。由于行政机关是具体运作国家权力和进行行政管理的机关,因而与立法机关和监督机关相比先天地具有某种优势,所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必须对它加以限制,否则,行政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演化为专制权力。
而就中国的历史实际来说,这种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政治场景则主要由中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小农的自然经济基础铸就。马克思说过:小农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因此,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的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局面,必须从改变小农的自然经济基础入手,建立和发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型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
实现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传统治国之道是我们的先辈留下的宝贵政治财富。但是,传统治国之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而且基本上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治国之道,并不能直接照搬到今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中。传统的治国之道要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作用,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指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现代转型,包括在治国理念、内容、形式和方法都由蒙昧、专制、人治转换到现代科学、民主、法治上来。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指对中国传统治国之道的提升和超越,主要在于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立足于解决当下和未来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创新性问题。正如罗斯·特里尔针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短板所提出的,中国国家治理“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只有实现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国家治理才能走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迈上持续稳定繁荣之途”。
如果从具体结合点来说,就是要将传统治理之道中的“政道”与“治道”置换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与“治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制度”和“治理”)放在一起,并对如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作出了全面部署,已足说明制度与治理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说,制度与治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从形式上看,制度是相对固化的,而治理是相对活化的;制度侧重于规范本身,而治理侧重于管理过程;制度侧重于文本载明的约束,而治理侧重于人的主体性活动。就两者关系而言,制度一般是治理的基础,而治理可能依赖制度进行,但也有可能不按制度办事而靠主观意志行事;制度的优势要转化为治理的效能,而治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制度之上;制度是否科学、合理,要由治理的成效来展示和检验,而治理的成效,既与制度有关,也与人的主体性活动有关。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与“治理”关系,是事关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否成功实现的根本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精准把握“制度”与“治理”关系逻辑,既要保持制度优势又要超越制度优势,既要重视治理效能又要超越治理效能,实现制度优势向“善制”的转换、治理效能向“善治”的转换,并且将“善制”与“善治”结合起来,以“善制”推动“善治”,又以“善治”促进“善制”,进而实现“更好的制度”和“更好的治理”的有机联动,从而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成功实现。
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既是对传统治国之道中“政道”与“治道”关系的超越,更是对传统治国之道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武汉大学教授)